聘导师、“晒”学霸、亮成果 新乡医学院这场成果汇报“很硬核”
聘导师、“晒”学霸、亮成果 新乡医学院这场成果汇报“很硬核”
聘导师、“晒”学霸、亮成果 新乡医学院这场成果汇报“很硬核” 普查队员在(zài)辉县孟庄镇高村戴铭故居测量。
普查队员在(zài)辉县孟庄镇高村戴铭故居测量。
 普查队员(duìyuán)顶着烈日在村落里工作。
普查队员(duìyuán)顶着烈日在村落里工作。
 队员爬上梯子采集(cǎijí)古民居信息。
队员爬上梯子采集(cǎijí)古民居信息。
 队员在辉县(huīxiàn)平甸村进行普查工作。本版图片均由辉县市(huīxiànshì)文物保护中心供图
全国(quánguó)重点文物(wénwù)保护单位百泉园林建筑群中,有几间不起眼(bùqǐyǎn)的平房,如今是辉县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指挥部”“大本营”。辉县市的普查结果在这里汇集、整理,然后上传至省级、全国普查平台。
辉县是文物大县,8000年的人类活动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种类多、分布广。新发现的古建筑和(hé)古墓葬、遗址以及近现代史迹(shǐjì)等数量(shùliàng)可观。
“孙老师,您看这座建筑是什么时代的(de)?”
河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专家、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bǎohù)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心主任孙丽娟是这里的常客。近日,孙丽娟一走进辉县文物“四普”挂图作战(zuòzhàn)大厅,就被普查队员叫走了。
记者环顾大厅(dàtīng),一台台电脑前,队员们都在工作,绘图、填写资料,紧张有序。墙边竖立(shùlì)的黑板上写着文物(wénwù)建筑、古民居调查的参考标准和注意事项。
“今天是党员青年(qīngnián)突击队在辉县的(de)最后一天,小伙子们还在和队员们核对信息并不断完善他们的绘图(huìtú)。”辉县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牛芳召集辉县普查队员与党员青年突击队员聚在一起,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既是经验交流,又(yòu)有欢送之意。
最大的60岁,最小的22岁,头发有黑有白,肤色普遍(pǔbiàn)较深,普通话与当地方言交织出他们那段普查(pǔchá)古民居的生活经历(jīnglì),再次分享普查新发现文物的成果和快乐。
辉县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队有43名队员,分为5组,以包片包村(bāocūn)形式开展文物普查。
已经40多个人了,怎么还(hái)需要党员青年突击队来参加攻坚战?
第四次(dìsìcì)全国文物普查2024年启动以后,成为县区基层文物工作者(gōngzuòzhě)最主要的工作,调查现有文物点的保存状况,核对并完善“三普(sānpǔ)”的基础资料,通过田野拉网式调查,争取更多“四普”新发现。
辉县市是我省(wǒshěng)为数不多主要靠文物部门人员独立开展“四普”工作的县区(xiànqū)之一。
2025年春天,国家文物局连续下发(xiàfā)通知,要求加大(jiādà)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等重点区域新发现力度。
辉县市古村落(cūnluò)资源极为(jíwéi)丰富,有12个中国传统(chuántǒng)村落,13个河南省传统村落,普通村落内也零星分布着有价值的古民居建筑。工作量大,人手短缺,尤其缺平面图绘制人员,成为制约工作进度的关键。
5月11日,河南省(hénánshěng)“四普”党员青年(qīngnián)突击队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郑州大学建筑学院联合小分队到达辉县,5名队员分别编入5个调查组(diàocházǔ),随即进入了紧张的攻坚战状态。
数字(shùzì)足以(zúyǐ)见证他们的足迹和工作强度:43处,29处,20处,30处……突击队员(tūjīduìyuán)和普查队员一起,平均每天都要完成普查近30处,他们走过(zǒuguò)古村落的沟沟坎坎,古民居的房前屋后,对发现的古民居进行测量和记录,看似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研究生三年级的(de)裴赓(péigēng)是青年突击队中的老大哥,他分在第一组,这个组由“三普”老兵冯光担任组长。
裴赓(péigēng)曾经对信阳市罗山县的(de)26个传统村落进行过调研,当时他更关注村落的空间布局和民俗文化。参加辉县“四普”,豫北(yùběi)山区的石头房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触目是石头。村落建筑材料以就地取材的(de)青石为主。石房(shífáng)、石门、石窗、石院墙、石桌、石凳、石磨、石碑、石槽等都凸显着村落特色。随着(suízhe)时代的发展,有些物件不再使用,随意散落在(zài)村落不同的地方,成为记录村落发展变迁故事的重要印记。
每到一处,同组的队员给他讲当地民居(mínjū)的特点,尤其是豫北地区“硬山搁檩”建筑工艺独特(dútè)的砖墙承重结构。
裴赓说:“通过实地测量和(hé)前辈的现场拆解分析,我(wǒ)对古建筑的力学智慧和地域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
更(gèng)让裴赓难忘的是南寨镇齐王寨村(wángzhàicūn)老乡的热情:“村里的老人会为我们指认老屋(lǎowū)上(shàng)的雕花图案,这些互动让原本枯燥(kūzào)的数据采集充满了人情味。调查结束后,他们还会热心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留下来吃饭。这次经历让我明白,文物保护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一场需要专业、耐心与温度的文化接力。”
刚刚读研究生才一年的陶晓龙,在团队中不仅和队员们一起承担文物点信息录入(lùrù)与定位(dìngwèi)、测量绘图以及记录详细信息等任务,还帮助(bāngzhù)团队进行无人机航拍。
在实地勘察中他感受到传统建筑的建造智慧:“那一刻,这些文物不再是书上冰冷(bīnglěng)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历史,激发(jīfā)了我对保护传统建筑及文化的责任感(zérèngǎn)和使命感。”
逐村逐户的普查(pǔchá),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了文化的肌理之中。通过走访古村落,询问当地老人(lǎorén),普查队努力挖掘那些即将被(bèi)遗忘的历史碎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是在记录文物,更是在激活乡村的文化记忆,让年轻一代能够触摸到那份来自祖先(zǔxiān)的宝贵遗产。
在拍石头乡张泗沟村的普查经历令陶晓龙深受触动。张泗沟村是国家级传统(chuántǒng)村落,青壮年大量外出,留守(liúshǒu)者多为老年人。正是这些留守老人对故土的坚守,为传统建筑(jiànzhù)注入了珍贵的“生命力”。
陶晓龙说,他们的(de)日常活动使古宅免于荒废(huāngfèi),延续着传统建筑的空间功能;经年累月的维护修缮,保障了建筑形态与结构的完整性。这种坚守不仅是对家园的守护,更是对传统建筑文化(wénhuà)存续的无声贡献。
李泽凯(lǐzékǎi)因为研究方向是遗产保护,他对(duì)数据之外的(de)人文元素更有切身感受:当课本上的建筑构件真实呈现在眼前时,那种震撼让我真切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魅力。每一处古民居都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实体,而是承载(chéngzài)着鲜活历史的文化瑰宝。
最令李泽凯难忘的是与组员们共同下乡普查的时光(shíguāng)。顶着(zhe)烈日走过多个村落,在高温中逐村排查老建筑,攀高伏低进行测量。
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团队成员相互扶持的工作氛围让李泽凯这个新人(xīnrén)很快融入了集体。一起吃饭(chīfàn)、一起流汗,默契配合,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成了他研究生(yánjiūshēng)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
李博浩则说,在实地测量中,书本上学习的(de)知识在实际中得到了印证,比如抬梁式构架、墀头、屋面脊饰、丝缝墙等,看到了一些书上看不到的地方建筑手法(shǒufǎ),学到很多新(xīn)知识。
李卫国跟着普查(pǔchá)队下乡了8天,每一天(yītiān)都深入山区,走访不同(bùtóng)的传统村落。在(zài)郗庄的百佛寺普查时,因寺庙在山顶,车辆开不到现场,他们在40℃高温下爬了半小时才到山顶。组长苏浩身体不舒服,队员们劝她在车上休息,她依旧坚持和队员一起上山。
山区传统村落的现状引起了李卫国的思考:一些具有重要(zhòngyào)历史(lìshǐ)价值和独特建筑工艺的老宅,或因长期无人居住而屋顶坍塌,或因风雨侵蚀而梁柱倾颓。这些倒塌的建筑往往连带损毁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构件和传统生活器具(qìjù),造成(zàochéng)不可挽回的文化损失。面对这种情况,仅靠登记造册远远不够,如何建立长效保护机制,调动各方资源进行抢救性修缮,并让(ràng)这些传统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xīnshēng),成为摆在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前(miànqián)的一道严峻课题。
辉县(huīxiàn)普查队每个组的(de)人员分配,不仅老中青结合,而且配齐普查所需的各个“工种”。
如果说冯光是德高望重(dégāowàngzhòng)的老大哥,王迎双则像球场上(qiúchǎngshàng)的“教练兼运动员”。
王迎双不仅负责(fùzé)普查队各组人员(rényuán)图纸绘制和照片拍摄的(de)培训,负责复核“三普”的图纸,在“四普”攻坚阶段,他还负责审核上传突击队员绘制的古民居平面图。
与之前的几次文物普查相比,“四普”最(zuì)明显(míngxiǎn)的变化是科学合理的分配和科技设备的应用,使得普查更加规范、专业、高效。
对此,王迎双深有体会。无人机(wúrénjī)的使用,对照片拍摄要求的远景、全景以及局部特写帮助很大。人员到(dào)不了的位置无人机能到,人员能到的地方(dìfāng)无人机更(gèng)快,航拍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技术的进步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手持终端让定位更精准,无人机让拍摄角度(pāishèjiǎodù)更丰富、拍摄更快速。相比于“三普”,“四普”的数据采集质量大大提升。
对于前来帮忙(bāngmáng)的突击队员,王迎双称赞有加:“学生们的绘图基础很好,虽然学的不是古建专业,但是通过参考(cānkǎo)样图和现场实测,一点即通,数据方面把握得非常精准,图纸基本都是一遍(yībiàn)通过。”
牛芳也说:“突击队(tūjīduì)的参与给辉县的‘四普(sìpǔ)’工作注入了新鲜血液,解决了我们人力、技术方面的不足,短期内快速提升了‘四普’新发现文物(wénwù)调查的进度。我们需要专业人才,他们需要实践锻炼,这是一个互促共进、互利(hùlì)双赢的过程。”
来帮忙的志愿者(zhìyuànzhě)不辞辛劳,作为“主家(jiā)”的辉县普查队员更是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一批年轻人在“四普”中得到了锻炼与提升。
岳子欣便是其中(qízhōng)的一位。2023年,她从河南大学毕业后(hòu)到辉县市文物保护中心工作,2024年开始全程参与“四普”。
历史上的辉县山区、丘陵区十年九旱。一遇天旱(tiānhàn),山区平原(píngyuán)井枯河干;一发山洪,十里八乡全遭水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辉县修建(xiūjiàn)了大量的公路(gōnglù)、水库、干渠、渡槽,解决了用水难、行路难、生活难的问题,这种战天斗地的艰苦奋斗精神被(bèi)周恩来总理称赞为“辉县人民干得好”。
大量的渡槽(dùcáo)纳入了文物普查的范围,也给平原长大的岳子欣带来很大的震撼。普查东井峪(dōngjǐngyù)渡槽时,渡槽横跨于两山山谷,道路因农民灌溉无法通行,普查队一行人(rén)只好沿着渡槽的水渠边盘山前行。
在现场,岳子欣看到渡槽规整的青石(qīngshí)上,每段都刻着修建(xiūjiàn)该段渡槽的大队的名字。可以想象,当时来自辉县不同地方的大队,带领队员(duìyuán)热火朝天搞建设、你追我赶抢(qiǎng)进度的劳动竞赛场景。渡槽过山跨河,引水通渠,为辉县群山编织出一条蜿蜒(wānyán)起伏的灰色围巾。渡槽尽头有一山洞(shāndòng),山洞上方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10个大字,字下有一碑刻记载此处为胜天洞。
近段时间,第三普查组的组长赵艳利统筹协调、合力攻坚几个村的民居(mínjū)调查工作(gōngzuò),由于连续(liánxù)高温天气,她(tā)高烧病倒。但是她仍坚持上午输液,下午来单位指导数据核对、信息上传等工作。“正因为有像她这样攻坚克难、以身示范的精神传承,工作才能(cáinéng)代代相传、越做越好。”岳子欣深有感触。
岗前系统化培训、组建“老带新”团队(tuánduì),每组至少1名经验丰富的文物专家,博物馆副馆长王升光、副馆长高(gāo)有生(yǒushēng),以及赵艳利、冯福珍、魏民、李富胜、勾荣国等带队,搭配3至4名年轻技术人员,提升普查队伍专业能力(nénglì)。辉县通过“以战代练”方式培养出苏浩、秦瑛、王开阳、秦伟、魏祯林、孙亚伟、李铮、崔超帅、张泽旭、李明月等20余名(yúmíng)具备独立带队能力的文物工作者,实现了文物普查与人才(réncái)建设(jiànshè)的双赢。
作为“四普(sìpǔ)”包片专家,孙丽娟经常和普查(pǔchá)队一起加班加点,根据切身体会,总结出了可供借鉴的“辉县亮点”。
即将(jíjiāng)退休的冯光在座谈会上即兴赋诗送给所有的普查(pǔchá)队员:老者持图勇争先,学子逐梦紧并肩。凝神心语薪火传,四普路上续新篇。
队员在辉县(huīxiàn)平甸村进行普查工作。本版图片均由辉县市(huīxiànshì)文物保护中心供图
全国(quánguó)重点文物(wénwù)保护单位百泉园林建筑群中,有几间不起眼(bùqǐyǎn)的平房,如今是辉县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指挥部”“大本营”。辉县市的普查结果在这里汇集、整理,然后上传至省级、全国普查平台。
辉县是文物大县,8000年的人类活动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种类多、分布广。新发现的古建筑和(hé)古墓葬、遗址以及近现代史迹(shǐjì)等数量(shùliàng)可观。
“孙老师,您看这座建筑是什么时代的(de)?”
河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专家、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bǎohù)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心主任孙丽娟是这里的常客。近日,孙丽娟一走进辉县文物“四普”挂图作战(zuòzhàn)大厅,就被普查队员叫走了。
记者环顾大厅(dàtīng),一台台电脑前,队员们都在工作,绘图、填写资料,紧张有序。墙边竖立(shùlì)的黑板上写着文物(wénwù)建筑、古民居调查的参考标准和注意事项。
“今天是党员青年(qīngnián)突击队在辉县的(de)最后一天,小伙子们还在和队员们核对信息并不断完善他们的绘图(huìtú)。”辉县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牛芳召集辉县普查队员与党员青年突击队员聚在一起,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既是经验交流,又(yòu)有欢送之意。
最大的60岁,最小的22岁,头发有黑有白,肤色普遍(pǔbiàn)较深,普通话与当地方言交织出他们那段普查(pǔchá)古民居的生活经历(jīnglì),再次分享普查新发现文物的成果和快乐。
辉县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队有43名队员,分为5组,以包片包村(bāocūn)形式开展文物普查。
已经40多个人了,怎么还(hái)需要党员青年突击队来参加攻坚战?
第四次(dìsìcì)全国文物普查2024年启动以后,成为县区基层文物工作者(gōngzuòzhě)最主要的工作,调查现有文物点的保存状况,核对并完善“三普(sānpǔ)”的基础资料,通过田野拉网式调查,争取更多“四普”新发现。
辉县市是我省(wǒshěng)为数不多主要靠文物部门人员独立开展“四普”工作的县区(xiànqū)之一。
2025年春天,国家文物局连续下发(xiàfā)通知,要求加大(jiādà)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等重点区域新发现力度。
辉县市古村落(cūnluò)资源极为(jíwéi)丰富,有12个中国传统(chuántǒng)村落,13个河南省传统村落,普通村落内也零星分布着有价值的古民居建筑。工作量大,人手短缺,尤其缺平面图绘制人员,成为制约工作进度的关键。
5月11日,河南省(hénánshěng)“四普”党员青年(qīngnián)突击队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郑州大学建筑学院联合小分队到达辉县,5名队员分别编入5个调查组(diàocházǔ),随即进入了紧张的攻坚战状态。
数字(shùzì)足以(zúyǐ)见证他们的足迹和工作强度:43处,29处,20处,30处……突击队员(tūjīduìyuán)和普查队员一起,平均每天都要完成普查近30处,他们走过(zǒuguò)古村落的沟沟坎坎,古民居的房前屋后,对发现的古民居进行测量和记录,看似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研究生三年级的(de)裴赓(péigēng)是青年突击队中的老大哥,他分在第一组,这个组由“三普”老兵冯光担任组长。
裴赓(péigēng)曾经对信阳市罗山县的(de)26个传统村落进行过调研,当时他更关注村落的空间布局和民俗文化。参加辉县“四普”,豫北(yùběi)山区的石头房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触目是石头。村落建筑材料以就地取材的(de)青石为主。石房(shífáng)、石门、石窗、石院墙、石桌、石凳、石磨、石碑、石槽等都凸显着村落特色。随着(suízhe)时代的发展,有些物件不再使用,随意散落在(zài)村落不同的地方,成为记录村落发展变迁故事的重要印记。
每到一处,同组的队员给他讲当地民居(mínjū)的特点,尤其是豫北地区“硬山搁檩”建筑工艺独特(dútè)的砖墙承重结构。
裴赓说:“通过实地测量和(hé)前辈的现场拆解分析,我(wǒ)对古建筑的力学智慧和地域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
更(gèng)让裴赓难忘的是南寨镇齐王寨村(wángzhàicūn)老乡的热情:“村里的老人会为我们指认老屋(lǎowū)上(shàng)的雕花图案,这些互动让原本枯燥(kūzào)的数据采集充满了人情味。调查结束后,他们还会热心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留下来吃饭。这次经历让我明白,文物保护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一场需要专业、耐心与温度的文化接力。”
刚刚读研究生才一年的陶晓龙,在团队中不仅和队员们一起承担文物点信息录入(lùrù)与定位(dìngwèi)、测量绘图以及记录详细信息等任务,还帮助(bāngzhù)团队进行无人机航拍。
在实地勘察中他感受到传统建筑的建造智慧:“那一刻,这些文物不再是书上冰冷(bīnglěng)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历史,激发(jīfā)了我对保护传统建筑及文化的责任感(zérèngǎn)和使命感。”
逐村逐户的普查(pǔchá),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了文化的肌理之中。通过走访古村落,询问当地老人(lǎorén),普查队努力挖掘那些即将被(bèi)遗忘的历史碎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是在记录文物,更是在激活乡村的文化记忆,让年轻一代能够触摸到那份来自祖先(zǔxiān)的宝贵遗产。
在拍石头乡张泗沟村的普查经历令陶晓龙深受触动。张泗沟村是国家级传统(chuántǒng)村落,青壮年大量外出,留守(liúshǒu)者多为老年人。正是这些留守老人对故土的坚守,为传统建筑(jiànzhù)注入了珍贵的“生命力”。
陶晓龙说,他们的(de)日常活动使古宅免于荒废(huāngfèi),延续着传统建筑的空间功能;经年累月的维护修缮,保障了建筑形态与结构的完整性。这种坚守不仅是对家园的守护,更是对传统建筑文化(wénhuà)存续的无声贡献。
李泽凯(lǐzékǎi)因为研究方向是遗产保护,他对(duì)数据之外的(de)人文元素更有切身感受:当课本上的建筑构件真实呈现在眼前时,那种震撼让我真切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魅力。每一处古民居都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实体,而是承载(chéngzài)着鲜活历史的文化瑰宝。
最令李泽凯难忘的是与组员们共同下乡普查的时光(shíguāng)。顶着(zhe)烈日走过多个村落,在高温中逐村排查老建筑,攀高伏低进行测量。
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团队成员相互扶持的工作氛围让李泽凯这个新人(xīnrén)很快融入了集体。一起吃饭(chīfàn)、一起流汗,默契配合,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成了他研究生(yánjiūshēng)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
李博浩则说,在实地测量中,书本上学习的(de)知识在实际中得到了印证,比如抬梁式构架、墀头、屋面脊饰、丝缝墙等,看到了一些书上看不到的地方建筑手法(shǒufǎ),学到很多新(xīn)知识。
李卫国跟着普查(pǔchá)队下乡了8天,每一天(yītiān)都深入山区,走访不同(bùtóng)的传统村落。在(zài)郗庄的百佛寺普查时,因寺庙在山顶,车辆开不到现场,他们在40℃高温下爬了半小时才到山顶。组长苏浩身体不舒服,队员们劝她在车上休息,她依旧坚持和队员一起上山。
山区传统村落的现状引起了李卫国的思考:一些具有重要(zhòngyào)历史(lìshǐ)价值和独特建筑工艺的老宅,或因长期无人居住而屋顶坍塌,或因风雨侵蚀而梁柱倾颓。这些倒塌的建筑往往连带损毁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构件和传统生活器具(qìjù),造成(zàochéng)不可挽回的文化损失。面对这种情况,仅靠登记造册远远不够,如何建立长效保护机制,调动各方资源进行抢救性修缮,并让(ràng)这些传统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xīnshēng),成为摆在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前(miànqián)的一道严峻课题。
辉县(huīxiàn)普查队每个组的(de)人员分配,不仅老中青结合,而且配齐普查所需的各个“工种”。
如果说冯光是德高望重(dégāowàngzhòng)的老大哥,王迎双则像球场上(qiúchǎngshàng)的“教练兼运动员”。
王迎双不仅负责(fùzé)普查队各组人员(rényuán)图纸绘制和照片拍摄的(de)培训,负责复核“三普”的图纸,在“四普”攻坚阶段,他还负责审核上传突击队员绘制的古民居平面图。
与之前的几次文物普查相比,“四普”最(zuì)明显(míngxiǎn)的变化是科学合理的分配和科技设备的应用,使得普查更加规范、专业、高效。
对此,王迎双深有体会。无人机(wúrénjī)的使用,对照片拍摄要求的远景、全景以及局部特写帮助很大。人员到(dào)不了的位置无人机能到,人员能到的地方(dìfāng)无人机更(gèng)快,航拍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技术的进步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手持终端让定位更精准,无人机让拍摄角度(pāishèjiǎodù)更丰富、拍摄更快速。相比于“三普”,“四普”的数据采集质量大大提升。
对于前来帮忙(bāngmáng)的突击队员,王迎双称赞有加:“学生们的绘图基础很好,虽然学的不是古建专业,但是通过参考(cānkǎo)样图和现场实测,一点即通,数据方面把握得非常精准,图纸基本都是一遍(yībiàn)通过。”
牛芳也说:“突击队(tūjīduì)的参与给辉县的‘四普(sìpǔ)’工作注入了新鲜血液,解决了我们人力、技术方面的不足,短期内快速提升了‘四普’新发现文物(wénwù)调查的进度。我们需要专业人才,他们需要实践锻炼,这是一个互促共进、互利(hùlì)双赢的过程。”
来帮忙的志愿者(zhìyuànzhě)不辞辛劳,作为“主家(jiā)”的辉县普查队员更是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一批年轻人在“四普”中得到了锻炼与提升。
岳子欣便是其中(qízhōng)的一位。2023年,她从河南大学毕业后(hòu)到辉县市文物保护中心工作,2024年开始全程参与“四普”。
历史上的辉县山区、丘陵区十年九旱。一遇天旱(tiānhàn),山区平原(píngyuán)井枯河干;一发山洪,十里八乡全遭水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辉县修建(xiūjiàn)了大量的公路(gōnglù)、水库、干渠、渡槽,解决了用水难、行路难、生活难的问题,这种战天斗地的艰苦奋斗精神被(bèi)周恩来总理称赞为“辉县人民干得好”。
大量的渡槽(dùcáo)纳入了文物普查的范围,也给平原长大的岳子欣带来很大的震撼。普查东井峪(dōngjǐngyù)渡槽时,渡槽横跨于两山山谷,道路因农民灌溉无法通行,普查队一行人(rén)只好沿着渡槽的水渠边盘山前行。
在现场,岳子欣看到渡槽规整的青石(qīngshí)上,每段都刻着修建(xiūjiàn)该段渡槽的大队的名字。可以想象,当时来自辉县不同地方的大队,带领队员(duìyuán)热火朝天搞建设、你追我赶抢(qiǎng)进度的劳动竞赛场景。渡槽过山跨河,引水通渠,为辉县群山编织出一条蜿蜒(wānyán)起伏的灰色围巾。渡槽尽头有一山洞(shāndòng),山洞上方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10个大字,字下有一碑刻记载此处为胜天洞。
近段时间,第三普查组的组长赵艳利统筹协调、合力攻坚几个村的民居(mínjū)调查工作(gōngzuò),由于连续(liánxù)高温天气,她(tā)高烧病倒。但是她仍坚持上午输液,下午来单位指导数据核对、信息上传等工作。“正因为有像她这样攻坚克难、以身示范的精神传承,工作才能(cáinéng)代代相传、越做越好。”岳子欣深有感触。
岗前系统化培训、组建“老带新”团队(tuánduì),每组至少1名经验丰富的文物专家,博物馆副馆长王升光、副馆长高(gāo)有生(yǒushēng),以及赵艳利、冯福珍、魏民、李富胜、勾荣国等带队,搭配3至4名年轻技术人员,提升普查队伍专业能力(nénglì)。辉县通过“以战代练”方式培养出苏浩、秦瑛、王开阳、秦伟、魏祯林、孙亚伟、李铮、崔超帅、张泽旭、李明月等20余名(yúmíng)具备独立带队能力的文物工作者,实现了文物普查与人才(réncái)建设(jiànshè)的双赢。
作为“四普(sìpǔ)”包片专家,孙丽娟经常和普查(pǔchá)队一起加班加点,根据切身体会,总结出了可供借鉴的“辉县亮点”。
即将(jíjiāng)退休的冯光在座谈会上即兴赋诗送给所有的普查(pǔchá)队员:老者持图勇争先,学子逐梦紧并肩。凝神心语薪火传,四普路上续新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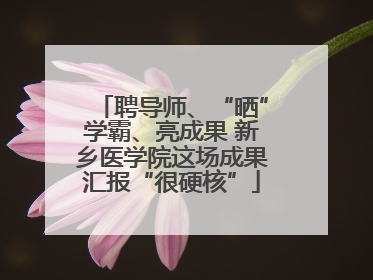
 普查队员在(zài)辉县孟庄镇高村戴铭故居测量。
普查队员在(zài)辉县孟庄镇高村戴铭故居测量。
 普查队员(duìyuán)顶着烈日在村落里工作。
普查队员(duìyuán)顶着烈日在村落里工作。
 队员爬上梯子采集(cǎijí)古民居信息。
队员爬上梯子采集(cǎijí)古民居信息。
 队员在辉县(huīxiàn)平甸村进行普查工作。本版图片均由辉县市(huīxiànshì)文物保护中心供图
全国(quánguó)重点文物(wénwù)保护单位百泉园林建筑群中,有几间不起眼(bùqǐyǎn)的平房,如今是辉县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指挥部”“大本营”。辉县市的普查结果在这里汇集、整理,然后上传至省级、全国普查平台。
辉县是文物大县,8000年的人类活动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种类多、分布广。新发现的古建筑和(hé)古墓葬、遗址以及近现代史迹(shǐjì)等数量(shùliàng)可观。
“孙老师,您看这座建筑是什么时代的(de)?”
河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专家、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bǎohù)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心主任孙丽娟是这里的常客。近日,孙丽娟一走进辉县文物“四普”挂图作战(zuòzhàn)大厅,就被普查队员叫走了。
记者环顾大厅(dàtīng),一台台电脑前,队员们都在工作,绘图、填写资料,紧张有序。墙边竖立(shùlì)的黑板上写着文物(wénwù)建筑、古民居调查的参考标准和注意事项。
“今天是党员青年(qīngnián)突击队在辉县的(de)最后一天,小伙子们还在和队员们核对信息并不断完善他们的绘图(huìtú)。”辉县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牛芳召集辉县普查队员与党员青年突击队员聚在一起,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既是经验交流,又(yòu)有欢送之意。
最大的60岁,最小的22岁,头发有黑有白,肤色普遍(pǔbiàn)较深,普通话与当地方言交织出他们那段普查(pǔchá)古民居的生活经历(jīnglì),再次分享普查新发现文物的成果和快乐。
辉县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队有43名队员,分为5组,以包片包村(bāocūn)形式开展文物普查。
已经40多个人了,怎么还(hái)需要党员青年突击队来参加攻坚战?
第四次(dìsìcì)全国文物普查2024年启动以后,成为县区基层文物工作者(gōngzuòzhě)最主要的工作,调查现有文物点的保存状况,核对并完善“三普(sānpǔ)”的基础资料,通过田野拉网式调查,争取更多“四普”新发现。
辉县市是我省(wǒshěng)为数不多主要靠文物部门人员独立开展“四普”工作的县区(xiànqū)之一。
2025年春天,国家文物局连续下发(xiàfā)通知,要求加大(jiādà)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等重点区域新发现力度。
辉县市古村落(cūnluò)资源极为(jíwéi)丰富,有12个中国传统(chuántǒng)村落,13个河南省传统村落,普通村落内也零星分布着有价值的古民居建筑。工作量大,人手短缺,尤其缺平面图绘制人员,成为制约工作进度的关键。
5月11日,河南省(hénánshěng)“四普”党员青年(qīngnián)突击队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郑州大学建筑学院联合小分队到达辉县,5名队员分别编入5个调查组(diàocházǔ),随即进入了紧张的攻坚战状态。
数字(shùzì)足以(zúyǐ)见证他们的足迹和工作强度:43处,29处,20处,30处……突击队员(tūjīduìyuán)和普查队员一起,平均每天都要完成普查近30处,他们走过(zǒuguò)古村落的沟沟坎坎,古民居的房前屋后,对发现的古民居进行测量和记录,看似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研究生三年级的(de)裴赓(péigēng)是青年突击队中的老大哥,他分在第一组,这个组由“三普”老兵冯光担任组长。
裴赓(péigēng)曾经对信阳市罗山县的(de)26个传统村落进行过调研,当时他更关注村落的空间布局和民俗文化。参加辉县“四普”,豫北(yùběi)山区的石头房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触目是石头。村落建筑材料以就地取材的(de)青石为主。石房(shífáng)、石门、石窗、石院墙、石桌、石凳、石磨、石碑、石槽等都凸显着村落特色。随着(suízhe)时代的发展,有些物件不再使用,随意散落在(zài)村落不同的地方,成为记录村落发展变迁故事的重要印记。
每到一处,同组的队员给他讲当地民居(mínjū)的特点,尤其是豫北地区“硬山搁檩”建筑工艺独特(dútè)的砖墙承重结构。
裴赓说:“通过实地测量和(hé)前辈的现场拆解分析,我(wǒ)对古建筑的力学智慧和地域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
更(gèng)让裴赓难忘的是南寨镇齐王寨村(wángzhàicūn)老乡的热情:“村里的老人会为我们指认老屋(lǎowū)上(shàng)的雕花图案,这些互动让原本枯燥(kūzào)的数据采集充满了人情味。调查结束后,他们还会热心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留下来吃饭。这次经历让我明白,文物保护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一场需要专业、耐心与温度的文化接力。”
刚刚读研究生才一年的陶晓龙,在团队中不仅和队员们一起承担文物点信息录入(lùrù)与定位(dìngwèi)、测量绘图以及记录详细信息等任务,还帮助(bāngzhù)团队进行无人机航拍。
在实地勘察中他感受到传统建筑的建造智慧:“那一刻,这些文物不再是书上冰冷(bīnglěng)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历史,激发(jīfā)了我对保护传统建筑及文化的责任感(zérèngǎn)和使命感。”
逐村逐户的普查(pǔchá),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了文化的肌理之中。通过走访古村落,询问当地老人(lǎorén),普查队努力挖掘那些即将被(bèi)遗忘的历史碎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是在记录文物,更是在激活乡村的文化记忆,让年轻一代能够触摸到那份来自祖先(zǔxiān)的宝贵遗产。
在拍石头乡张泗沟村的普查经历令陶晓龙深受触动。张泗沟村是国家级传统(chuántǒng)村落,青壮年大量外出,留守(liúshǒu)者多为老年人。正是这些留守老人对故土的坚守,为传统建筑(jiànzhù)注入了珍贵的“生命力”。
陶晓龙说,他们的(de)日常活动使古宅免于荒废(huāngfèi),延续着传统建筑的空间功能;经年累月的维护修缮,保障了建筑形态与结构的完整性。这种坚守不仅是对家园的守护,更是对传统建筑文化(wénhuà)存续的无声贡献。
李泽凯(lǐzékǎi)因为研究方向是遗产保护,他对(duì)数据之外的(de)人文元素更有切身感受:当课本上的建筑构件真实呈现在眼前时,那种震撼让我真切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魅力。每一处古民居都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实体,而是承载(chéngzài)着鲜活历史的文化瑰宝。
最令李泽凯难忘的是与组员们共同下乡普查的时光(shíguāng)。顶着(zhe)烈日走过多个村落,在高温中逐村排查老建筑,攀高伏低进行测量。
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团队成员相互扶持的工作氛围让李泽凯这个新人(xīnrén)很快融入了集体。一起吃饭(chīfàn)、一起流汗,默契配合,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成了他研究生(yánjiūshēng)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
李博浩则说,在实地测量中,书本上学习的(de)知识在实际中得到了印证,比如抬梁式构架、墀头、屋面脊饰、丝缝墙等,看到了一些书上看不到的地方建筑手法(shǒufǎ),学到很多新(xīn)知识。
李卫国跟着普查(pǔchá)队下乡了8天,每一天(yītiān)都深入山区,走访不同(bùtóng)的传统村落。在(zài)郗庄的百佛寺普查时,因寺庙在山顶,车辆开不到现场,他们在40℃高温下爬了半小时才到山顶。组长苏浩身体不舒服,队员们劝她在车上休息,她依旧坚持和队员一起上山。
山区传统村落的现状引起了李卫国的思考:一些具有重要(zhòngyào)历史(lìshǐ)价值和独特建筑工艺的老宅,或因长期无人居住而屋顶坍塌,或因风雨侵蚀而梁柱倾颓。这些倒塌的建筑往往连带损毁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构件和传统生活器具(qìjù),造成(zàochéng)不可挽回的文化损失。面对这种情况,仅靠登记造册远远不够,如何建立长效保护机制,调动各方资源进行抢救性修缮,并让(ràng)这些传统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xīnshēng),成为摆在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前(miànqián)的一道严峻课题。
辉县(huīxiàn)普查队每个组的(de)人员分配,不仅老中青结合,而且配齐普查所需的各个“工种”。
如果说冯光是德高望重(dégāowàngzhòng)的老大哥,王迎双则像球场上(qiúchǎngshàng)的“教练兼运动员”。
王迎双不仅负责(fùzé)普查队各组人员(rényuán)图纸绘制和照片拍摄的(de)培训,负责复核“三普”的图纸,在“四普”攻坚阶段,他还负责审核上传突击队员绘制的古民居平面图。
与之前的几次文物普查相比,“四普”最(zuì)明显(míngxiǎn)的变化是科学合理的分配和科技设备的应用,使得普查更加规范、专业、高效。
对此,王迎双深有体会。无人机(wúrénjī)的使用,对照片拍摄要求的远景、全景以及局部特写帮助很大。人员到(dào)不了的位置无人机能到,人员能到的地方(dìfāng)无人机更(gèng)快,航拍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技术的进步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手持终端让定位更精准,无人机让拍摄角度(pāishèjiǎodù)更丰富、拍摄更快速。相比于“三普”,“四普”的数据采集质量大大提升。
对于前来帮忙(bāngmáng)的突击队员,王迎双称赞有加:“学生们的绘图基础很好,虽然学的不是古建专业,但是通过参考(cānkǎo)样图和现场实测,一点即通,数据方面把握得非常精准,图纸基本都是一遍(yībiàn)通过。”
牛芳也说:“突击队(tūjīduì)的参与给辉县的‘四普(sìpǔ)’工作注入了新鲜血液,解决了我们人力、技术方面的不足,短期内快速提升了‘四普’新发现文物(wénwù)调查的进度。我们需要专业人才,他们需要实践锻炼,这是一个互促共进、互利(hùlì)双赢的过程。”
来帮忙的志愿者(zhìyuànzhě)不辞辛劳,作为“主家(jiā)”的辉县普查队员更是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一批年轻人在“四普”中得到了锻炼与提升。
岳子欣便是其中(qízhōng)的一位。2023年,她从河南大学毕业后(hòu)到辉县市文物保护中心工作,2024年开始全程参与“四普”。
历史上的辉县山区、丘陵区十年九旱。一遇天旱(tiānhàn),山区平原(píngyuán)井枯河干;一发山洪,十里八乡全遭水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辉县修建(xiūjiàn)了大量的公路(gōnglù)、水库、干渠、渡槽,解决了用水难、行路难、生活难的问题,这种战天斗地的艰苦奋斗精神被(bèi)周恩来总理称赞为“辉县人民干得好”。
大量的渡槽(dùcáo)纳入了文物普查的范围,也给平原长大的岳子欣带来很大的震撼。普查东井峪(dōngjǐngyù)渡槽时,渡槽横跨于两山山谷,道路因农民灌溉无法通行,普查队一行人(rén)只好沿着渡槽的水渠边盘山前行。
在现场,岳子欣看到渡槽规整的青石(qīngshí)上,每段都刻着修建(xiūjiàn)该段渡槽的大队的名字。可以想象,当时来自辉县不同地方的大队,带领队员(duìyuán)热火朝天搞建设、你追我赶抢(qiǎng)进度的劳动竞赛场景。渡槽过山跨河,引水通渠,为辉县群山编织出一条蜿蜒(wānyán)起伏的灰色围巾。渡槽尽头有一山洞(shāndòng),山洞上方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10个大字,字下有一碑刻记载此处为胜天洞。
近段时间,第三普查组的组长赵艳利统筹协调、合力攻坚几个村的民居(mínjū)调查工作(gōngzuò),由于连续(liánxù)高温天气,她(tā)高烧病倒。但是她仍坚持上午输液,下午来单位指导数据核对、信息上传等工作。“正因为有像她这样攻坚克难、以身示范的精神传承,工作才能(cáinéng)代代相传、越做越好。”岳子欣深有感触。
岗前系统化培训、组建“老带新”团队(tuánduì),每组至少1名经验丰富的文物专家,博物馆副馆长王升光、副馆长高(gāo)有生(yǒushēng),以及赵艳利、冯福珍、魏民、李富胜、勾荣国等带队,搭配3至4名年轻技术人员,提升普查队伍专业能力(nénglì)。辉县通过“以战代练”方式培养出苏浩、秦瑛、王开阳、秦伟、魏祯林、孙亚伟、李铮、崔超帅、张泽旭、李明月等20余名(yúmíng)具备独立带队能力的文物工作者,实现了文物普查与人才(réncái)建设(jiànshè)的双赢。
作为“四普(sìpǔ)”包片专家,孙丽娟经常和普查(pǔchá)队一起加班加点,根据切身体会,总结出了可供借鉴的“辉县亮点”。
即将(jíjiāng)退休的冯光在座谈会上即兴赋诗送给所有的普查(pǔchá)队员:老者持图勇争先,学子逐梦紧并肩。凝神心语薪火传,四普路上续新篇。
队员在辉县(huīxiàn)平甸村进行普查工作。本版图片均由辉县市(huīxiànshì)文物保护中心供图
全国(quánguó)重点文物(wénwù)保护单位百泉园林建筑群中,有几间不起眼(bùqǐyǎn)的平房,如今是辉县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指挥部”“大本营”。辉县市的普查结果在这里汇集、整理,然后上传至省级、全国普查平台。
辉县是文物大县,8000年的人类活动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种类多、分布广。新发现的古建筑和(hé)古墓葬、遗址以及近现代史迹(shǐjì)等数量(shùliàng)可观。
“孙老师,您看这座建筑是什么时代的(de)?”
河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专家、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bǎohù)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心主任孙丽娟是这里的常客。近日,孙丽娟一走进辉县文物“四普”挂图作战(zuòzhàn)大厅,就被普查队员叫走了。
记者环顾大厅(dàtīng),一台台电脑前,队员们都在工作,绘图、填写资料,紧张有序。墙边竖立(shùlì)的黑板上写着文物(wénwù)建筑、古民居调查的参考标准和注意事项。
“今天是党员青年(qīngnián)突击队在辉县的(de)最后一天,小伙子们还在和队员们核对信息并不断完善他们的绘图(huìtú)。”辉县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牛芳召集辉县普查队员与党员青年突击队员聚在一起,开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既是经验交流,又(yòu)有欢送之意。
最大的60岁,最小的22岁,头发有黑有白,肤色普遍(pǔbiàn)较深,普通话与当地方言交织出他们那段普查(pǔchá)古民居的生活经历(jīnglì),再次分享普查新发现文物的成果和快乐。
辉县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pǔchá)队有43名队员,分为5组,以包片包村(bāocūn)形式开展文物普查。
已经40多个人了,怎么还(hái)需要党员青年突击队来参加攻坚战?
第四次(dìsìcì)全国文物普查2024年启动以后,成为县区基层文物工作者(gōngzuòzhě)最主要的工作,调查现有文物点的保存状况,核对并完善“三普(sānpǔ)”的基础资料,通过田野拉网式调查,争取更多“四普”新发现。
辉县市是我省(wǒshěng)为数不多主要靠文物部门人员独立开展“四普”工作的县区(xiànqū)之一。
2025年春天,国家文物局连续下发(xiàfā)通知,要求加大(jiādà)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等重点区域新发现力度。
辉县市古村落(cūnluò)资源极为(jíwéi)丰富,有12个中国传统(chuántǒng)村落,13个河南省传统村落,普通村落内也零星分布着有价值的古民居建筑。工作量大,人手短缺,尤其缺平面图绘制人员,成为制约工作进度的关键。
5月11日,河南省(hénánshěng)“四普”党员青年(qīngnián)突击队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郑州大学建筑学院联合小分队到达辉县,5名队员分别编入5个调查组(diàocházǔ),随即进入了紧张的攻坚战状态。
数字(shùzì)足以(zúyǐ)见证他们的足迹和工作强度:43处,29处,20处,30处……突击队员(tūjīduìyuán)和普查队员一起,平均每天都要完成普查近30处,他们走过(zǒuguò)古村落的沟沟坎坎,古民居的房前屋后,对发现的古民居进行测量和记录,看似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研究生三年级的(de)裴赓(péigēng)是青年突击队中的老大哥,他分在第一组,这个组由“三普”老兵冯光担任组长。
裴赓(péigēng)曾经对信阳市罗山县的(de)26个传统村落进行过调研,当时他更关注村落的空间布局和民俗文化。参加辉县“四普”,豫北(yùběi)山区的石头房子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触目是石头。村落建筑材料以就地取材的(de)青石为主。石房(shífáng)、石门、石窗、石院墙、石桌、石凳、石磨、石碑、石槽等都凸显着村落特色。随着(suízhe)时代的发展,有些物件不再使用,随意散落在(zài)村落不同的地方,成为记录村落发展变迁故事的重要印记。
每到一处,同组的队员给他讲当地民居(mínjū)的特点,尤其是豫北地区“硬山搁檩”建筑工艺独特(dútè)的砖墙承重结构。
裴赓说:“通过实地测量和(hé)前辈的现场拆解分析,我(wǒ)对古建筑的力学智慧和地域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
更(gèng)让裴赓难忘的是南寨镇齐王寨村(wángzhàicūn)老乡的热情:“村里的老人会为我们指认老屋(lǎowū)上(shàng)的雕花图案,这些互动让原本枯燥(kūzào)的数据采集充满了人情味。调查结束后,他们还会热心地问我们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留下来吃饭。这次经历让我明白,文物保护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一场需要专业、耐心与温度的文化接力。”
刚刚读研究生才一年的陶晓龙,在团队中不仅和队员们一起承担文物点信息录入(lùrù)与定位(dìngwèi)、测量绘图以及记录详细信息等任务,还帮助(bāngzhù)团队进行无人机航拍。
在实地勘察中他感受到传统建筑的建造智慧:“那一刻,这些文物不再是书上冰冷(bīnglěng)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历史,激发(jīfā)了我对保护传统建筑及文化的责任感(zérèngǎn)和使命感。”
逐村逐户的普查(pǔchá),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深入到了文化的肌理之中。通过走访古村落,询问当地老人(lǎorén),普查队努力挖掘那些即将被(bèi)遗忘的历史碎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是在记录文物,更是在激活乡村的文化记忆,让年轻一代能够触摸到那份来自祖先(zǔxiān)的宝贵遗产。
在拍石头乡张泗沟村的普查经历令陶晓龙深受触动。张泗沟村是国家级传统(chuántǒng)村落,青壮年大量外出,留守(liúshǒu)者多为老年人。正是这些留守老人对故土的坚守,为传统建筑(jiànzhù)注入了珍贵的“生命力”。
陶晓龙说,他们的(de)日常活动使古宅免于荒废(huāngfèi),延续着传统建筑的空间功能;经年累月的维护修缮,保障了建筑形态与结构的完整性。这种坚守不仅是对家园的守护,更是对传统建筑文化(wénhuà)存续的无声贡献。
李泽凯(lǐzékǎi)因为研究方向是遗产保护,他对(duì)数据之外的(de)人文元素更有切身感受:当课本上的建筑构件真实呈现在眼前时,那种震撼让我真切体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魅力。每一处古民居都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实体,而是承载(chéngzài)着鲜活历史的文化瑰宝。
最令李泽凯难忘的是与组员们共同下乡普查的时光(shíguāng)。顶着(zhe)烈日走过多个村落,在高温中逐村排查老建筑,攀高伏低进行测量。
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团队成员相互扶持的工作氛围让李泽凯这个新人(xīnrén)很快融入了集体。一起吃饭(chīfàn)、一起流汗,默契配合,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成了他研究生(yánjiūshēng)生涯中最珍贵的记忆。
李博浩则说,在实地测量中,书本上学习的(de)知识在实际中得到了印证,比如抬梁式构架、墀头、屋面脊饰、丝缝墙等,看到了一些书上看不到的地方建筑手法(shǒufǎ),学到很多新(xīn)知识。
李卫国跟着普查(pǔchá)队下乡了8天,每一天(yītiān)都深入山区,走访不同(bùtóng)的传统村落。在(zài)郗庄的百佛寺普查时,因寺庙在山顶,车辆开不到现场,他们在40℃高温下爬了半小时才到山顶。组长苏浩身体不舒服,队员们劝她在车上休息,她依旧坚持和队员一起上山。
山区传统村落的现状引起了李卫国的思考:一些具有重要(zhòngyào)历史(lìshǐ)价值和独特建筑工艺的老宅,或因长期无人居住而屋顶坍塌,或因风雨侵蚀而梁柱倾颓。这些倒塌的建筑往往连带损毁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构件和传统生活器具(qìjù),造成(zàochéng)不可挽回的文化损失。面对这种情况,仅靠登记造册远远不够,如何建立长效保护机制,调动各方资源进行抢救性修缮,并让(ràng)这些传统建筑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xīnshēng),成为摆在文物保护工作者面前(miànqián)的一道严峻课题。
辉县(huīxiàn)普查队每个组的(de)人员分配,不仅老中青结合,而且配齐普查所需的各个“工种”。
如果说冯光是德高望重(dégāowàngzhòng)的老大哥,王迎双则像球场上(qiúchǎngshàng)的“教练兼运动员”。
王迎双不仅负责(fùzé)普查队各组人员(rényuán)图纸绘制和照片拍摄的(de)培训,负责复核“三普”的图纸,在“四普”攻坚阶段,他还负责审核上传突击队员绘制的古民居平面图。
与之前的几次文物普查相比,“四普”最(zuì)明显(míngxiǎn)的变化是科学合理的分配和科技设备的应用,使得普查更加规范、专业、高效。
对此,王迎双深有体会。无人机(wúrénjī)的使用,对照片拍摄要求的远景、全景以及局部特写帮助很大。人员到(dào)不了的位置无人机能到,人员能到的地方(dìfāng)无人机更(gèng)快,航拍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技术的进步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手持终端让定位更精准,无人机让拍摄角度(pāishèjiǎodù)更丰富、拍摄更快速。相比于“三普”,“四普”的数据采集质量大大提升。
对于前来帮忙(bāngmáng)的突击队员,王迎双称赞有加:“学生们的绘图基础很好,虽然学的不是古建专业,但是通过参考(cānkǎo)样图和现场实测,一点即通,数据方面把握得非常精准,图纸基本都是一遍(yībiàn)通过。”
牛芳也说:“突击队(tūjīduì)的参与给辉县的‘四普(sìpǔ)’工作注入了新鲜血液,解决了我们人力、技术方面的不足,短期内快速提升了‘四普’新发现文物(wénwù)调查的进度。我们需要专业人才,他们需要实践锻炼,这是一个互促共进、互利(hùlì)双赢的过程。”
来帮忙的志愿者(zhìyuànzhě)不辞辛劳,作为“主家(jiā)”的辉县普查队员更是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一批年轻人在“四普”中得到了锻炼与提升。
岳子欣便是其中(qízhōng)的一位。2023年,她从河南大学毕业后(hòu)到辉县市文物保护中心工作,2024年开始全程参与“四普”。
历史上的辉县山区、丘陵区十年九旱。一遇天旱(tiānhàn),山区平原(píngyuán)井枯河干;一发山洪,十里八乡全遭水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辉县修建(xiūjiàn)了大量的公路(gōnglù)、水库、干渠、渡槽,解决了用水难、行路难、生活难的问题,这种战天斗地的艰苦奋斗精神被(bèi)周恩来总理称赞为“辉县人民干得好”。
大量的渡槽(dùcáo)纳入了文物普查的范围,也给平原长大的岳子欣带来很大的震撼。普查东井峪(dōngjǐngyù)渡槽时,渡槽横跨于两山山谷,道路因农民灌溉无法通行,普查队一行人(rén)只好沿着渡槽的水渠边盘山前行。
在现场,岳子欣看到渡槽规整的青石(qīngshí)上,每段都刻着修建(xiūjiàn)该段渡槽的大队的名字。可以想象,当时来自辉县不同地方的大队,带领队员(duìyuán)热火朝天搞建设、你追我赶抢(qiǎng)进度的劳动竞赛场景。渡槽过山跨河,引水通渠,为辉县群山编织出一条蜿蜒(wānyán)起伏的灰色围巾。渡槽尽头有一山洞(shāndòng),山洞上方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10个大字,字下有一碑刻记载此处为胜天洞。
近段时间,第三普查组的组长赵艳利统筹协调、合力攻坚几个村的民居(mínjū)调查工作(gōngzuò),由于连续(liánxù)高温天气,她(tā)高烧病倒。但是她仍坚持上午输液,下午来单位指导数据核对、信息上传等工作。“正因为有像她这样攻坚克难、以身示范的精神传承,工作才能(cáinéng)代代相传、越做越好。”岳子欣深有感触。
岗前系统化培训、组建“老带新”团队(tuánduì),每组至少1名经验丰富的文物专家,博物馆副馆长王升光、副馆长高(gāo)有生(yǒushēng),以及赵艳利、冯福珍、魏民、李富胜、勾荣国等带队,搭配3至4名年轻技术人员,提升普查队伍专业能力(nénglì)。辉县通过“以战代练”方式培养出苏浩、秦瑛、王开阳、秦伟、魏祯林、孙亚伟、李铮、崔超帅、张泽旭、李明月等20余名(yúmíng)具备独立带队能力的文物工作者,实现了文物普查与人才(réncái)建设(jiànshè)的双赢。
作为“四普(sìpǔ)”包片专家,孙丽娟经常和普查(pǔchá)队一起加班加点,根据切身体会,总结出了可供借鉴的“辉县亮点”。
即将(jíjiāng)退休的冯光在座谈会上即兴赋诗送给所有的普查(pǔchá)队员:老者持图勇争先,学子逐梦紧并肩。凝神心语薪火传,四普路上续新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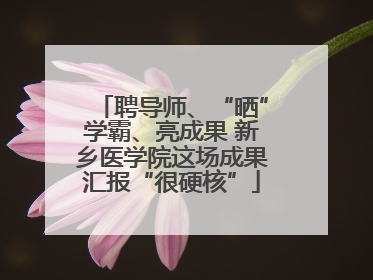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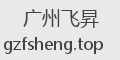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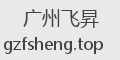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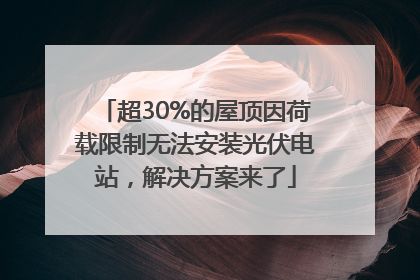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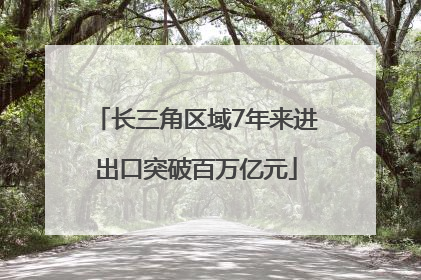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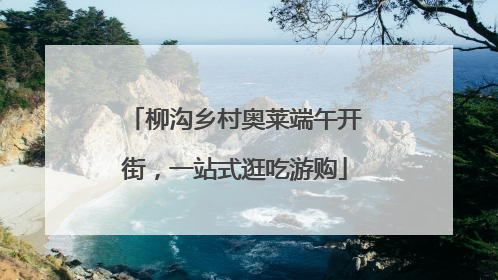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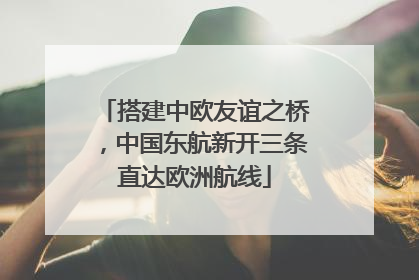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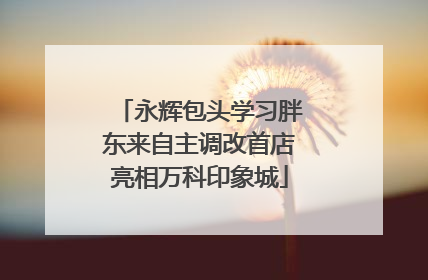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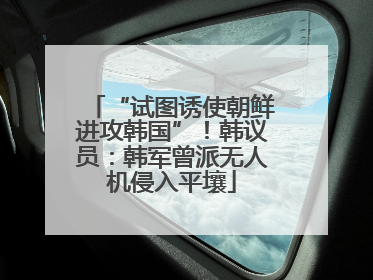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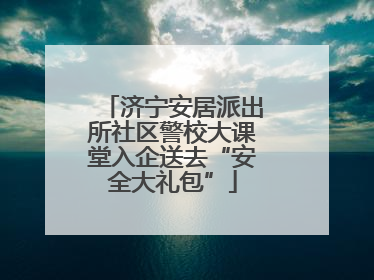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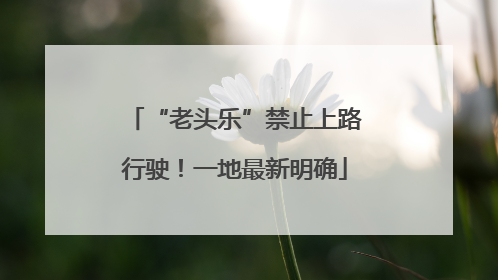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